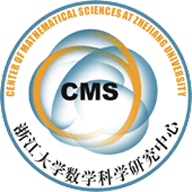
浙大杰出校友、著名数学家杨忠道先生不幸去世
时间: 2005-09-16 来源:数学科学研究中心浙大杰出校友、著名数学家杨忠道先生不幸去世
惊悉,浙江大学杰出校友、著名数学家杨忠道先生因病于近日不幸去世,享年82岁。杨忠道先生早年就读浙江大学,曾长期担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数学系主任,1968年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杨忠道先生曾多次来浙江大学访问讲学,非常关心我校数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他生前曾多次表示,非常希望来浙江大学为大学生开基础课。他的去世是国际数学界的重大损失,也是浙江大学数学学科的重大损失,在此表示沉痛哀悼。

著名数学家杨忠道先生简介
杨忠道(Chung-Tao Yang),著名拓扑学家。
1923年5月生于浙江省平阳县;
1942年毕业于浙江省立温州中学高中部;
1946年毕业于国立浙江大学数学系;
1946-1948年在浙江大学数学系任助教;
1948-1950年在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担任助理研究员;
1949-1950年任台湾大学讲师;
1952年获美国Tulane大学数学博士学位;
1952-1954年任Illinois大学研究助理;
1954-1956年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访问;
1956-1991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数学系任教
1978-1983年间曾担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数学系主任;
1968年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1972年入选美国Who is Who名人辞典。
杨忠道先生在射影几何学,一般拓扑学,代数拓扑学,李群等领域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证明了著名的Dyon猜想,在一般拓扑学中有著名的杨忠道定理。他的儿子Deane Yang是美国Polytechnic大学数学系教授。
杨忠道院士访谈
张海潮老师 访问,叶德财 纪录
(2000年1月17日)
「做数学要有一股傻劲和拼劲。」----杨院士给后学
我是在浙江省平阳县一个乡下地方长大的。现在属浙江省苍南县平等乡。那时候平阳县很落后,全县没有一所初级中学,小学也不多。不过当地有一所私立初小,所以我自然地在那里就读到四年级。上五年级时附近就没有学校了,最近的离家五里。天天走那么远去上学非体弱的我所能做到,何况乡下多泥路,一下雨不好走,所以上高小时我就住在学校的宿舍里,到周末才回家。
上四年级时,数学教师黄仲迪先生利用逻辑方法,讨论鸡兔同笼的问题,激发起我对数学的兴趣,我喜爱数学,从此就开始了。仲迪先生是一位十分难得的小学教师。他家境清寒,只读了半年初中就辍学了。不过他努力自修,以教小学谋生,调教出来不少好学生。他给学生们的印象是口才好,而且智识丰富。1983年我回故乡探亲,他得到消息后,特地到我弟弟家找我,互谈半个世纪中的演变。1991年我在回家乡探亲时,县教育委员会安排我对数十位中学数学教师讲学一星期。我乘机提出邀请仲迪先生为贵宾,参加讲学前的典礼。在典礼中我介绍仲迪先生是我读数学的启蒙老师,希望大家以后以他为榜样。
因为当时平阳县没有初中,我上的初中在别的县里,离开家约一百四十里。乡下的交通很不方便,从家里去学校须换舟车近十次,得花十五小时,所以一学期中难得回家一次。父亲是地主的后代,到他当家时只有足以餬口的田地,对我上初中的费用负担的很辛苦。所以我初中毕业后没有让我考高中,但是停学在家不是办法,于是安排我在当地初小教二年级,继续让我用自己赚来的钱先去上高中,再看以后如何。因为失过学,我成熟多了,也感到求学的可贵,所以在高中三年中,我的成绩总在班上前三名,因此得到公费,使我完成高中学业。读高中时我的数理化都不错,以数学被老师及同学们认为最出色。文科的成绩不坏,但是那都是靠死背强记得来的。
在艰苦的生活下,父亲知道祖产不能凭,也知道他年纪大了必须我去赡养他,因此他鼓励我去念工科。当时我很喜欢数学,也是理化的好学生,于是去向数学教师陈仲武先生请教。仲武先生早就了解我,而且有他个人的判断。他没有犹豫的说:「你当然去念数学,如果连你也不去念,还有什么人该去念呢﹖!」凭仲武先生这一句话,我就义无反顾去读数学了。
那时候平阳县的教育虽然很落后,但是出了两位数学家。第一位是姜立夫教授,他于1919年获得美国哈佛大学数学博士学位,是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第二位是苏步青教授,他于1931年获得日本东北帝大数学博士学位,是台湾大学理学院第一任院长。两人都是中央研究院第 一届的院士。我从小就听过他们的大名,但到四十年代才认识他们。
高中毕业会考,我的成绩不错,可以保送进国立大学就读。当时我决定进浙江大学,从苏步青先生学习现代数学。抗战期间许多地方被日军占领,浙江大学已迁到贵州去了。所以大学一年级我是在浙大龙泉分校念的,到第二年才到贵州去。
当时浙大数学系在贵州省湄潭县,步青先生是系主任。说起来很难使现在年轻人相信,那时候系里没有职员,系主任必须总管系里大小事务。幸亏全系师生的总人数只有三四十人,非有要事不会去麻烦系主任的。步青先生对学生亲如子女,照顾得很周到。我是他的小同乡,觉得他对我更好些。
步青先生的努力,大概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及得上,这是由下述的事实见到的。1944年步青先生家里有七个小孩,最大的上高一,最小的刚出生。那时候教授的薪水不高,他没有办法顾人帮忙。一家九口的家事靠师母一个人做,事实上不可能,所以步青先生和大的几个小孩都得帮忙。那时候数学系没有办公室,师生门有事情找他只好直接去他家。因为没有电话,无法预先约定时间,所以白天和晚上,随时有人登门拜访。在那种情形下,他不但处理系务、教课,而且继续作他自己的研究工作,也指导年轻教师做研究。每年总有几篇论文发表在外国数学杂志上,真是谈何容易。步青先生很能利用他的时间,好多次到他家时,见到他一只手抱小孩,同时阅读数学书籍,还用另一只手写笔记。说他一个人做两三个人的工作,不算太过分吧!有这样一位老师摆在前面做榜样,想偶而偷点小赖也找不到借口了。
四十年代浙大数学系的课程和现在台大数学系的课程大同小异。我读过的课程,在一年级时有微积分和微分方程,在二年级时有高等微积分、级数概论、立体解析几何及选修的数论和偏微分方程,在三年级时有综合几何、近世代数和复变量函数,在四年级时有微分几何、实变量函数和数学研究。在浙大我没有念过泛函分析、拓朴学,原因是没有教师能教授这两门课。据记忆,在大学四年中,我的数学课的成绩没有低于九十分者,好像每学期的总平均都高过九十分。我让步青先生惊讶的不是这些高分数却是在二年级读理论力学时得九十分。理论力学是数学系学生的必修课程,但可待至三四年级时去读。这是一门出名难读的课程,数学系好学生去读时,有时也很困难,甚至不及格须补考,使数学系很不满意。怪不得步青先生见到我的高分时,笑着对我说:「数学系多年来的怨气,给你一下子出光了。」事实上物理系学生读这门课同样有困难,和我一起读理论力学的同学有十多人,及格只有五人,而且都是数学系的。
上三年级的综合几何课是步青先生亲授。他鼓励学生阅读课外参考书籍,因此我读了一本的德文版射影几何。也许他认为我还能担当一些工作,于是指派我义务替数学系管理图书杂志,也能就近翻阅易懂的数据。因此我上四年级时,自己找题目完成一篇论文。步青先生觉得还不错,结果那篇论文在美国发表(《Duke J. of Math.》,1947 )。大学毕业后,我留在系里任助教,两年中又自己找题目作论文,除在国内发表的外,又有一篇在美国数学杂志上发表,再有一篇在阿根廷数学杂志上发表。如何去找题目,求解答,主要是受步青先生的训练,当时不够深入。文章虽然可以刊登出来,到后来再看,太肤浅了。
1947年起政局相当混乱,想在学校里安心做研究工作事实上不可能,于是我征得步青先生的同意,于1948年夏天,去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从代所长陈省身教授学习代数拓朴。目的是希望在两三年中,学到一些新的 知识,再回到浙大数学系。
没有料到去了中央研究院后,时局急转直下,数学研究所的研究活动完全停顿,同时陈省身教授决定接受邀请,去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研究。接着教育部发表历史语言研究所博斯年所长将继任台湾大学校长,于是他提议将中央研究院迁往台湾。但是可以想象,如物理研究所、化学研究所等有实验室设备的研究所根本不可能考虑搬迁,所以最后决定搬迁的只有历史语言研究所和数学研究所,而且只准许部份人员去台湾。
根据我的了解,数学研究所的安排是所长姜立夫先生和代所长陈省身先生共同决定的,一方面保全图书杂志,另方面保全部份研究实力,以备来日东山再起。随数学研究所到台湾的研究工作人员,除立夫先生外,有副研究员王宪钟先生和胡世桢先生及助理员三人,即廖山涛、陈杰和杨忠道。王、胡两位先生曾在英国得数学博士学位,打算到台湾后在美国觅教职(后来都是中央研究院院士,已过世)。至于三位助理员 ,将协助他们去美国留学。我知道有一位助理员要求去台湾被拒绝了,我是到所最晚的助理员,为什么被挑中,则非我所知了。
到了台湾后,院方告诉数学所四位单身人员,没有办法安排我们在台北居住,暂居的地方是杨梅镇。到了杨梅,才知道居住的地方是在一仓库里。历史语言研究所书籍很多,堆积在杨梅的一所仓库里。临时把两个书箱排在一起,在上面摆一个塌塌米,就做为我们每个人的床铺了。仓库的建设,并没有准备在里面住人的,窗户小,而且高逾一丈。屋顶很高,只有近屋顶地方,才有几盏昏暗的电灯。大门一关,黑暗的很。加上杨梅镇风大,非关大门不可,所以几天后大家都知道白天非出去不可。杨梅只是一个小镇,没有图书馆,没有公园,一条小街上只有几间小铺子,进去后若不照顾生意,两三分钟就得出来,所以我们四人决定必须自己设法回台北找居住地方。经过努力,也透过私人关系,我们四人在台北厦门街台湾大学一个招待所里,找到了一间六塌塌米大的房间。因为没有壁橱,四个人睡在四角落,让皮箱堆在中央。虽然如此,比在杨梅镇好多了,至少在白天可以上公园、逛街、逛书店。那时候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写一封信都不容易,更谈不到做什么工作。
后来我知道师院附中(即后来的师大附中)急需一位数学教师,教高二三班的大代数,于是去向立夫先生请示。 他说反正目前无法工作,先利用这机会解决眼前的困难再看吧!所以我决定接那份教职,但是有条件的,就是说必须有单身宿舍可以住。因此我在师院附中执教了一学期。
到1949年夏天,生活情况好多了,但人事上有变化。立夫先生去了广州,决定留在那里帮岭南大学创办数学系。王、胡两位先生在美国找到教职,离开了台湾。陈杰因惦念未婚妻,取道广州回四川。廖山涛和我两人正式在台大数学系兼任讲师,而且有宿舍可住。由1949至1950,我教一班土木系的微积分和一班机械系的微分方程,其中许振荣先生去美国进修,他的高等几何课也由我代授。记得那班上的同学有王典荣(已在香港中文大学退休)和吴青木(已在淡江大学退休)。又在微分方程班上的吴达森同学,后来转读数学系,留美而成为美国大学的教授 。
1950年王、胡两先生帮我获得Teaching Fellowship,去美国Tulane University (Louisiana) 读博士学位,旅费是中央研究院给的,到那时我才知道,这个安排在数学研究所搬迁到台湾之前,已经取得院方同意。同时,廖山涛亦去美国留学,也受到同样的待遇。
初到美国时,我的英语不好(后来也没有好过,只是能够应付而已。这一点我觉得去美国留学的人必须注意!),一天到晚羞于开口。也许在十多位数学系的研究生中,我是唯一的非美国人,所以大家对我都很照顾。第一学期我选了四门数学课及一门阅读报告。其中一位授课老师是 A.D. Wallace 教授,也是我博士论文的指导教授,他教课的方法是他的师祖 R.L. Moore 创造的,将课程内容分做许多小命题,预先发给学生。上课时他要学生上台去证明,他自己坐在台下听。一个学生没完成时叫第二个上去,一个小时没有完成就留到下一小时再继续,他自己绝不帮忙。我的英语虽然不好,在他的课中表现得不错,所以一开始就给他一个好印象。他对学生们很友善,常常在课余时到研究生的办公室,谈谈数学,也讲笑话。见到我的时候,总要提出或大或小的数学问题,嘱我多想想。第二个学期一开始,他嘱我去读法国数学家H. Cartan 在哈佛大学教授代数拓朴的讲义。
第一学年结束后系里给我生活费,嘱我在暑期中好好用功。Cartan讲义中一个主要成果是“For compact Hausdorff spaces, certain two cohomology theories are equivalent”在 Wallace 教授的课程中,我学到了fully normal spaces的概念。经过几个星期的思考,我觉得 Cartan讲义中那成果可以被扩充到 fully normal spaces。当我向Wallace教授提起这一发现时,他十分惊讶,于是抽空和我讨论我的构想。几星期后他逐渐相信我的构想很可能是对的,可以作为我的博士论文,于是他开始筹划我的前途。Tulane University是美国南方一所好大学,在全美也称得上二三流学校,不过数学系在我之前只出过不到十位的博士,于是Wallace教授通过系主任请研究院给我一个例外待遇。得博士学位照惯例必须修满二十个学分,但Wallace教授觉得为我,为数学系,反不如早点给我博士学位,而且推荐我去研究活动多的地方,求进一步的发展,所以系里特许我于第二学期不选课,专心去书写博士论文。
Wallace教授的初意是希望我去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任讲师,使能从 N. Steenrod教授做代数拓朴的研究,但是没有成功。1952年秋天我去了University of Illinois数学系当博士后研究,每周教授三小时,同时参加系里研究活动。那时候系里有一位代数拓朴的教授 D.G. Bourgin,带五、六位博士研究生,研究的主要对象是 (F.J.) Dyson 的猜测。我不但去听 Bourgin 教授的课,也去参加他率领的讨论班。经过一年的努力,我得到了 一个Dyson猜测的证明,Bourgin 教授知道后十分惊讶,当时只说他自己也做得差不多了。这件事使我很尴尬,于是去向陈省身先生请教。他给我一个建议,说最好的解决方法,是两人合写一篇文章去发表,不过必须由他提出来才是。如果他不提,我应该自己发表,不过文章中应提及听说 Bourgin 教授有一独立的证明。结果我的文章于1954年发表在《Annals of Math》上,Bourgin的文章于1955年发表在瑞士一数学杂志上。在University of Illinois 我停留了两年。我在那里的时候,施拱星先生正在那里读博士学位。周元燊院士去读博士学位恰在我离开之后,我曾帮忙向系方推荐他。
我在 University of Illinois 所写的两篇文章颇引人注意,同时Wallace 教授继续努力推荐我去普林斯顿做研究。1954年秋天,我获得美国国科会一年的资助,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研究,主要的对象是将Dyson猜测再扩充,使亦包括 Borsuk-Ulam 定理。一切安排是Wallace教授透过 D. Montgomery 教授才办成功的。
Montgomery教授出身于小型的大学,所以他十分同情非名校出身但工作能力强的年轻数学工作者,也很同情来自他国学者,他的理由是由名校出身的美国人已经有很多的机会,无须他人多帮忙。每年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研究的数学工作者在五十人之上,年轻的较多,在大家的心目中,以 Montgomery 教授人缘最好。
我的研究计划,半年内就完成了。顺着同样路线做下去,前途并不乐观,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另找途径。正在那时候,Montgomery教授和 L. Zippen 教授合写了一本书《Topological Transformation Group》。前半本解答 Hilbert's Fifth Problem,那是四年前他们合作的 一篇文章和一篇A.M. Gleason 文章所得到的成果,后半本讨论拓朴变换群。因为这些是当时大家公认最重要的贡献,当然非好好读不可,于是我自荐帮忙那本书的校对工作。读完了全书,我觉得可以考虑某些问题,于是向Montgomery教授请教。他听了以后,告诉我其中一个问题,正是他和H. Samelson 教授研究的对象,立即表示欢迎我加入他们的行列。因为这个偶然的机缘,使我在那两年中,和他们两人合写了两篇文章。
1956年秋天我去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简称宾大)工作,一个原因是宾大数学系有一位教授在高等研究院进修,知道我的研究工作,也知道Montgomery 教授和我合作,竭力向系里推荐我。另一个原因是宾大距离普林斯顿相当近,不论自己驾车或搭火车,一个多小时可以到达,使我有较多机会向Montgomery 教授请教。在宾大我一共工作了三十五年,起先是助理教授,1958年被提升为副教授,1961年被提升为正教授。在职期间,曾兼任数学系里研究生部主任四年,数学系系主任五年。在我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的有L.Mann(1959),后来任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数学系系主任多年,1961年有苏竞存,他于1954年毕业于台大物理系,后来改念数学,现在是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数学系教授。
来宾大教书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常去看Montgomery教授,后来他干脆每星期留下一天,让我去和他讨论数学。这样维持了二十多年,合写了二十多篇文章。
1968年我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72年列名于《美国名人录》(Who's Who in Ameri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