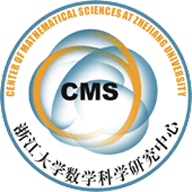|
题记
杨乐认为,我国由一个人口大国转变为人才大国需要三个层次的共同努力:一是大力发展义务教育,使全民科学文化素养得以大幅度提高。二是每个领域都需要大量本领域的专业人才。通过研究生教育,培养出更多的人才,满足各项事业的需求。三是各学科领域都应拥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学术领军人物。
遗憾的是,在杨乐看来,这三个层面都存在问题,需要大力改进。
杨院士在北京的办公室是名副其实的“斗室”。推门进入时,已经有人在访谈。见我们进门,杨院士向那位同志道了声歉意:“这是我约定的客人”,随即将我们领到了下一层的会客室。
信心
话题自然从胡锦涛总书记来看望杨乐说起。
杨乐眯起了眼,似乎在回忆之中:“我们谈得很愉快。锦涛同志指出,中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要依靠科学技术。我向锦涛同志说起数学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数学和其他学科与高新技术之间的相融关系。总体上说,对中国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问题
受教育要平等
说到了人才的培养,杨乐开始皱眉头。
杨院士先从教育说起:“基础教育应该搞好,这关系到全民的素质,我们国家各条战线都需要高素质的人才。”
“但是,我们的教育出现了一些问题”,杨乐的眉头皱得更紧:“我们的一些制度和规定有可能将农民和城市困难居民的子女排斥在外。如果我们不大力关注,一些人可能因此失学,一些人会受到干扰,还有一些人会因为交不起各种费用而不能专心学习。这部分人数量不是很少。”
杨乐回忆说:“在我以往的接触中,即使在很差的环境,即使是十分贫困的家庭,也能够出人才。我国的尖端人才中,包括一些学科的台柱教授,很多就是在十分贫困的经济条件下成才的。美国也一样。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有目共睹,教育事业也在发展,但是在这一点上出了问题。我们要呼吁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否则有些人才难以顺利成长。”
别将“奥数”当产业
杨乐认为,一些父母不切实际地望子成龙也是当代教育的一个误区,他们把在“奥数”一类的竞赛上获奖当作子女成才的标志。一些教育工作者迎合了家长和学生的这种心态,把“奥数”当作一项产业来做。“教育部门与许多学者已经呼吁了多次,这种状况却未得到根本改变,而且受到了强有力的抵制。有位在北京开书店的台湾人孙先生曾对王元先生说:那些搞‘奥数’的,收入比你高若干倍!他们给中小学生讲‘奥数’,按课时收费,开价比两院院士的演讲高得多。”
杨乐介绍说,在国外,一些好的大学,在录取新生时也考虑学生的综合素质,包括参加一些课外活动与竞赛的经历。一些中学生参加“奥数”竞赛,只是一种兴趣。而我国的许多学校,则将“奥数”异化了,从高中、初中到小学,大家参加,临时突击,强化训练,灌输技巧,而不是强调能力的提高。技巧并不是灵活运用的能力。“他们的目的只是拿奖牌,因为只要拿到了奖牌,就可以在升大学时加分。”
“国外也有些竞赛,是在较长时间里(如一学期)培养一些同学的兴趣,提高创新能力,有较好效果。去年香港举办了首届这样的竞赛,其做法值得借鉴。”
少带几个研究生
杨乐话锋一转,谈到了研究生教育。“二十多年来,研究生教育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但也出现了新问题,就是有些院系与导师过分关注经济效益,而轻视了人才的培养。”
杨乐介绍说,在研究生教育中,少数教授每人带几十位研究生,有的听说带上百个。“他们并不是从培养、训练人才的角度考虑,而是为研究生联系好了企业与公司,让他们在那里干活。”
杨乐告诉记者,带一名研究生,需要导师的精心培育,从打基础到指导撰写论文,需要全过程培训。“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同时带10人应该已经是极限:需要有10个有价值的研究课题,一二周就得听研究生一次汇报,了解他们学了哪些文献,有什么心得与进步,会有哪些困难并且需要花一二个小时与研究生单独讨论,互相交流。要完成这个流程,同时带五六十乃至上百位研究生根本不可能。”
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杨乐已经在“两会”上正式提出,建议限制导师带研究生的人数——同时带研究生的人数不得超过10名。“国家确实紧缺的个别专业需要超过10人限制时,应该经过国家学位委员会或相应高层机构的严格审批,而且也应限定超出人数的数量。”
杨乐对一些研究生培养单位要求研究生必须发表规定数量的论文才可以毕业的规定也不以为然。他说,各门学科,各所学校,情况很不相同,不宜作出硬性的统一规定。否则,有的研究生就选容易做的小题目,拼凑论文,个别甚至抄袭、作假。“有的院校过分强调SCI的期刊与论文数量,这并不科学,SCI期刊论文数量质量相差悬殊。用这种简单的数量统计来决定研究生能否毕业对人才培养极为不利。”
领军人物和官本位
我们不知不觉地谈到了中国的学科领军人物。杨乐认为,一个国家的科技强不强,主要看领军人物的水平和数量。“就像看你们文汇报,就是看你们报纸有多少名记者,写了多少有影响的稿件。”
杨乐表示,“我国科技界需要高水平的领军人物,我们希望有年轻人超越自己。我们殷切希望年轻的学术带头人的学识和水平不断提高,以缩短与世界的差距,甚至与世界水平持平或者超越世界水平。过去中国出过这样的人物,今后也一定能出现。这就需要我们有远大的胸怀,把中国的发展纳入世界发展的宏图之中。”
杨乐认为,官本位意识滞缓了科技领军人物的步伐。有的人总是习惯于将官放在学术之上,在排名单时,甚至将一名副处长排在学部委员院士之前。排名其实也体现了一种体制和观念。在一些管理部门,他们首先看的是“官”的级别。这种体制和观念对年轻人的影响很大。
杨乐表示,做学问是很艰苦的事,需要坐长期的冷板凳,任何学问不可能一下子就会有满意的结果。“我有这样的经历,一进入科研的攻坚阶段,就往往是食而不知其味,晚上只睡四五个小时,满脑子都在想遇到的问题,希望能够找到解决的办法,一想就是一整天,往往会持续三到四个礼拜。这必须集中精力,不能有丝毫干扰。而且需要有充沛的精力,我在年轻时能行,现在已经力不从心,就像一名高级指挥官,主要是指挥与参谋,到第一线拼刺刀不行了。”
杨乐继续评说“官本位”:现有的问题是,有时将研究领域和课题与官位混在一起。其实,两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这种现状对年轻人影响的结果,就是诱导年轻人去走官场的路,做学问辛辛苦苦得不到的东西,有了官位后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
不找关系会吃亏
杨乐谈到了记者写丘成桐先生的那篇《数学之美》(见本报2004年12月27日“近距离”专版):“丘先生提到的学术权贵和评议制度,值得我们认真思改。自从我国1981年设立了学位制度以来,我就是国务院博士点评审委员会成员。当时的风气很正,没有人上门找关系,评得上评不上听其自然,评委讨论时客观公正,评定结果绝对不会向院校通风报信,由国务院学位办统一发布。我至今觉得应该这样。但这些年来情况有了变化。”
托人找关系已不是十分个别的现象。“也有单位来找我。我告诉他们:你们找了也是白找。但他们说,不找就会吃亏。国务院学位办三令五申,不准搞这些名堂。但这些情况却早已是半公开化。
杨乐又谈到了丘成桐先生:“我与丘先生不是一个研究领域,但我深知他的学术水平。即使是欧美等国的某些一流数学家,也认为丘先生是近四分之一世纪以来数学成就最大的数学大师。全球近七十年来有几十位费尔兹奖获得者,华裔仅丘先生一位,而且是成就突出的一位。丘先生33岁拿到费尔兹奖,是‘少年登高科’。他的杰出贡献还在于他对祖国数学发展的推动,他是40来岁精力最旺盛时就开始做这项事业。十多年来,他在海外募捐,支持国内的数学研究,举办三个数学研究中心,关注与培养青年人才的成长;倡导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提升学术水平。”
“我们需要培养一大批数学家”
杨乐院士是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的首届院长。1996年,经丘成桐先生牵线,由香港著名实业家陈启宗兄弟及其叔父出资3000万元,在中科院建立了晨兴数学中心。中心建立了崭新的体制,由学术委员会领导中心工作,聘请丘成桐担任主任,杨乐担任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
晨兴数学中心运行8年,已经取得了卓著的成效。
“我们每年都会确定六七个,乃至十个研究专题,这些专题涉及基础数学、计算数学和应用数学的重要领域。我们鼓励国内外的专家学者来申请这些专题研究。并约请一些年轻的、有基础的优秀博士或博士后到我们中心,集中3至6个月的时间搞研究。这几个月很重要,一方面可以有较长的时间集中搞研究,另一方面我们会邀请同领域世界最高水平的学者来中心为这些优秀博士和博士后演讲。有了几次这样的接触和交流,水平会提高很快,就有可能成为某一领域的领军人物。
“每年国内大约有150人到我们中心做研究,他们中大约有70%多的人来自大学,还有20%几来自研究院所。他们的基础本来就扎实,有了中心这样的环境,加上与国际最高水平的学者进行交流,他们的眼界会变得更开阔,有许多人已经出了成果,写出了十分优秀的学术论文,发表在国际一流的刊物上。
“一些国外的学者到我们晨兴中心来讲学,看到了我们所做的工作,他们都很感动。他们对我说,一批又一批年轻人,为了研究数学,自动聚在一起,在现在的世界已经很难找到。我告诉他们,中国经历了‘文革’,基础科学遭受了严重破坏,拉大了与世界的差距。我们需要缩短这种差距,必须培养一大批数学家。
“晨兴中心十分注重发挥各大学数学方面学术带头人的作用,与他们合作做好晨兴中心的专题研究。比如复旦大学的洪家兴,如今已经是中科院院士,他几次到我们晨兴中心搞研究,在几何分析上有出色的成果。南京大学的程崇庆,如今在动力系统领域是领军人物。还有中山大学的朱熹平教授,今年才42岁,在几何分析与数学物理上很有贡献,这次在香港颁发的晨兴奖,他获得晨兴数学银奖。其他还有一批优秀的年轻学者。
“我特别要说一说‘晨兴’,这是香港实业家陈启宗家族的贡献。如今已经有三个晨兴数学研究中心,一个在香港中文大学,一个在北京中科院,一个在浙江大学,都是丘(成桐)先生主持其事的。香港中文大学的数学所建得最早,已经有10年。这10年香港的数学发展很快,该所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次与浙江大学数学中心刘克峰一起获得晨兴数学金奖的辛周平就是香港中文大学数学所的执行主任。
“陈启宗家族值得称道的是,他们为祖国数学的发展慷慨捐赠,却毫不张扬。他们还捐资设立了晨兴数学奖,邀请了若干位一流专家作评委,而他们自己却从不干预评审工作。”
数学人生
这个华罗庚、陈省身先生口中的师弟,终于实现了少年时的梦想,中国人杨乐的名字已经写到了外国的数学书上。
杨乐是十岁多时考入南通中学的,初二时,杨乐就对数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因为开始有了代数和几何。原来复杂的运算居然可以用英文字母代替,很困难的题设了未知数就能够立方程简单地予以解决。几何也一样。有了兴趣,上课就很专心,课堂上的知识基本上是当堂消化。下课时杨乐就做那些题目。很快,其数学成绩就与同学拉开了距离,考100分是很平常的事。
杨乐当时发现书中的定理、名称许多是以外国数学家的名字命名,杨乐认为,中国人也可以为数学发展作出贡献,用中国人名字命名的定理,也应该可以写在未来的数学书上。
1956年,他考入了北京大学数学系,当时还不满17岁。他在北大数学系读了6年。
1962年,杨乐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所,有幸成了熊庆来先生的弟子。华罗庚、陈省身先生都当过熊先生的弟子。后来,华先生、陈先生都曾亲切地称杨乐为师弟。
熊先生自称是“老马识途”,确实有道理。当时,有关函数的历史经典书籍文献足有好几个书柜,单凭他和学长张广厚等人自己的摸索,会找不着门。熊先生只指定看一本并不厚的书,仅一百多页,是函数值分布现代理论的奠基人所写。这本书确实是领他们入门的最佳版本。其他类似的书有几倍的篇幅,水平远不如这本书。
当然,书还需自己看。杨乐读书有个习惯,不会满足于只从表面上读懂弄通书本上的那些定理,总要去揣摩定理创始人的思路。这办法挺管用,他与张广厚合作,研究函数值分布论中的“亏值”和“奇异方向”课题,这是困扰国际上该领域达半个多世纪的难题,国际数学界的许多优秀专家已经倾注了他们无数的精力。以往数学界只把“亏值”和“奇异方向”作为两个互不相连的重要概念进行探索,他们则反其道而行之,终于有了新收获。“亏值”和“奇异方向”虽构成一对矛盾,但其相互间的关系并不是对立、排异的,而是相互依赖、有机联系的。他们还解决了“亏值”和“奇异方向”方面的其他难题。在“亏值”数目估计方面,国外数学家仅仅是在附加特殊条件下取得一些结果,而他们却是在普遍条件下获得了准确的结果;对于“奇异方向”的研究,长期没有解决“奇异方向”分布规律的研究,而他们的研究成果干净彻底地解决了这个长期悬而未决的难题。
遗憾的是,在十年浩劫期间,中国与世界的科学界之间恍若隔世。1964年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海曼提出的函数论问题,他们早已解决;1969年区律欣在国际顶尖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其认知水平未能超过杨乐与张广厚1965年的论文。他在研究生期间发表在《中国科学》杂志上的论文,尤其是有关幅角分布的论文,处于当时世界该领域的最前沿。但由于中国与世界隔绝,他们的成果并不被国际同行立即认知。
1978年4月13日,在苏黎士国际函数论大会上,杨乐报告了他们的研究成果,被与会的数学家称为“惊人的成果”。美国出版的一份有关数学研究的报告评价说,他们的成果“既新颖又深刻”,与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一样是纯粹数学方面“第一流的工作”。美国著名函数论专家区律欣也评价说:“杨乐与张广厚在北京领导着一个成果丰硕、欣欣向荣的学派”。
1977年之后,杨乐应邀赴美、苏、德、英、日、瑞典、芬兰、瑞士、新西兰、以色列等六十多所著名大学讲学,多次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在伦敦举办的国际函数论大会上,他被推举为第一次大会的主席。少年时的梦想也终于实现,中国人杨乐的名字已经写到了外国的数学书上。
人物简介
杨乐,1939年生于江苏南通,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并考取中科院数学研究所研究生。任中科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所长。20世纪70年代对整函数与亚纯函数亏值与波莱尔方向间的联系作了深入研究。与张广厚合作最先发现并建立了这两个基本概念之间的具体联系。引进了新的奇异方向并对奇异方向的分布给出了完备的解答。对全纯与亚纯函数族的正规性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建立了正规性与不动点间的联系。与英国学者合作证明了著名数学家立特沃德的一个猜想。对亚纯函数的导数的总亏量与整函数的亏值数目作出了精确估计。由于在函数模分布论、辐角分布论、正规族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突出而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何梁何利奖、陈嘉庚奖和华罗庚数学奖,2004年12月又荣获陈省身奖(见右图)。八十年代初,杨乐担任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副所长,后来又长期担任所长。在任职期间,他十分注意使研究所成为学术氛围浓郁、环境宽松的研究机构。他非常关注研究生的培养与青年学者的成长。当年在数学所深造的青年,诸如张寿武、刘克峰、周向宇、张伟平等,已成为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杰出学者。
1998年,中国科学院首批知识创新工程试点,数学所、应用数学所、系统科学所、计算数学所进行体制上的整合与重大改革,成立了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杨乐被委任为首任院长。研究院在体制改革、凝聚学术方向、人才培养、学术交流与创新文化等方面克服了重大困难,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
曾任中国科学院主席团委员、数理学院副主任、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协常委、中国数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奖励委员会委员等职。现任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协荣誉委员。1980年11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即中科院院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