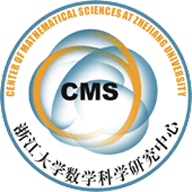
文汇报:数学之美
时间: 2004-12-27 来源:数学科学研究中心 | |
| 2004年12月27日 星期一 | |
| 数学之美(附照片) |
| 作者:万润龙 日期:2004.12.27 版次:4 |
数学之美 ■撰稿/本报记者万润龙 摄影/卢绍庆 ——与其他数学家不同的是,丘成桐把数学推向了中国,推向了整个华裔世界。这是他的伟大之处。 ——认为我的奋斗目标是奖项,是成名成家,那是不对的。这些都不是本人研究的首要目标。我对数学的兴趣,源于人类智能足以参悟自然的欣喜。从几何上看,大自然的美是永恒不朽的。 直击国内数学时弊 2002年8月,记者曾与陪同著名科学家霍金来杭州的丘成桐有过几次深入的交谈。当时的感觉是,丘成桐不回避记者提出的所有问题,而且实话实说,观点鲜明。他在浙江科技会堂为浙江科技界人士作演讲时历数了中国科技界和高校的陋习,以及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逐渐拉大的差距,令许多听讲者汗颜。在场的媒体记者群情振奋,耳目一新。但丘成桐的演讲稿却没有能够推上绝大多数媒体的版面。文汇报的“演讲”版几乎全文刊登了他的演讲,一时间文汇报在网上的点击率猛增,网民们大呼“振聋发聩”。 上周,在香港与丘先生相遇,丘成桐实话实说的秉性有增无减。 数学不等于奥数,前者是做研究,后者是做题目,用奥数班培养出来的只有考试能力,没有思想能力。做奥数竞赛绝对成就不了数学大国 丘成桐对内地中小学中的“奥数热”现象大泼冷水。他说:做奥数竞赛绝对成就不了数学大国。数学其实是做研究,而奥数却只是做题目。奥数金奖只能证明考试的能力,而不是研究的能力。研究的根本是自己找问题,而奥数训练的不是这个,只知道去做别人的题目,而不知道去做自己的题目。“有些地方将学生聚在一起,进行专门的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培训。获了奖又怎么样?”丘成桐告诉记者,他教过好几个得过奥数金奖的中国留学生,这些学生的学问太狭窄,对考试有能力,对思想没能力,最后连毕业都困难。 本报记者告诉丘成桐:上海已经作出决定,在中小学取消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其他一些城市也在考虑取消奥数赛。 对此,丘成桐深感欣慰。他说,应该鼓励孩子多看一些名人传记,这能够培养孩子对数学和基础科学产生兴趣,比上奥数班有用多了。 中国距离数学大国还有相当距离,基础学科投资太少,评审制度不透明,年轻学者为利益巴结学术权贵 本届数学大会是开放式的,有两次大中学生与数学大师面对面的交流。学生们的提问有的不失肤浅,却是经过一番思考和准备的。 有好几位学生在不同的场合问了同样一个问题:中国距数学大国和数学强国有多远? 丘成桐回答:与国外比还有相当差距,“我们已经或正在做大量的努力,包括成立数学研究所,包括向中青年华人数学家颁发‘晨兴数学奖’,希望能加快中国数学的发展,但这些努力无法改变中国在数学领域研究的落后状况。” 丘教授表示,中国对基础科学的投资太少,评审制度又不够透明,经费的分配、教授的提职、评奖等都是由少数几个人说了算,而这少数几个人又往往代表不了专家的意见。一些年轻学者为了得到提升和获奖,就去巴结这些学术权贵。一旦得到学术权贵的赏识,就可以名利双收。真正有才华的年轻学者,只好选择出国一途。更加好笑的是,居然由媒体来评选学者,这本来应该由同行评价的事,变成了商业操作。 香港中学生的论文水平已经达到美国名校学士论文的水平,其能力在内地很少见 12月18日晚,近百位香港中学生与数学大师站在了一起。他们都是“恒隆数学奖”的得主。这项奖是由丘先生创意,由香港恒隆集团出资设立的。恒隆集团还应丘先生的倡导而设立了数学“晨兴奖”。 那天晚上,丘先生特别高兴。他不时与一队又一队的中学生合影、交谈。记者参加了他们的交谈,发现他们的研究别出心裁。有一队的参赛选题是剖析某部世界畅销小说中父亲与儿子的关系,学生们用数学来体现这种关系。还有一队到商场进行了调查,根据电梯人流和顾客结构的数据,整理出独有的数学公式…… 丘成桐告诉记者,香港中学生的数学水平之高,连国际上著名的数学家都“另眼相看”。丘成桐称这些中学生的论文“已经达到美国名校学士论文的水平”。他介绍说,“恒隆数学奖”比赛,参赛队伍需要自找研究题目及资料,最后参赛者还需参加答辩,接受国际著名数学家的提问。这次比赛吸引了113支参赛队伍,他们分别来自香港63所学校。最终有15队获奖,最年轻的入围者才14岁。 记者询问丘先生:这种场景在内地多不多?丘先生摇摇头:没有。然后对记者说:你把这种对比写出来。 一个人和三个数学研究所 今年3月,中国政府为了表彰丘成桐教授对中国数学事业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授予他2003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就在这次颁奖仪式上,丘教授作了简短而又热情洋溢的发言。他说,他感到很荣幸,因为他为促进中国和其它国家的科学交流所作的努力被中国政府所认识。他说,他在香港中文大学接受高等教育,有幸能够比较全面地接受中国文化教育。优美的中国文学对他的思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为自己的祖国不断发展的悠久文明而骄傲。在他专心作基础科学研究的同时,也把促进科学的发展,特别是祖国科学的发展作为终身的责任。 丘成桐教授十分关注中国数学事业的发展,并为此花费了大量时间和心血。自1979年应华罗庚教授邀请回国访问与讲学以来,他通过培养人才、成立研究所和捐款等形式,支持和促进我国的数学研究。至今年3月,已累计捐款人民币约2856万元、美金298万元。 值得一说的是丘先生创办的三个数学研究机构。 1994年,他在香港中文大学创建了数学所,并任所长 1996年,在中科院的支持下,在北京建立了晨兴数学中心并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 2002年,支持在浙江大学成立了浙大数学科学研究中心,并出任中心主任 在本次香港之行中,记者恰与著名数学家杨乐院士同住一家酒店,杨教授是中国科学院晨兴数学中心学术委员会的副主任。杨教授告诉记者,中科院晨兴数学中心成立于1996年6月10日,是在丘成桐先生的推动下,由中国科学院和香港晨兴集团共同出资兴办的。创办数学中心的初衷是努力培养和造就优秀的青年数学家,做出具有国际水平的研究成果,形成学术气氛浓郁的研究环境。 丘成桐是晨兴数学中心的学术委员会主任。 在三个数学研究机构中,丘成桐寄予厚望的是浙江大学数学科学中心。他是这个中心学术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全部由国际公认一流的数学大师担任,包括谷超豪、杨乐、励建书、林芳华、李骏、刘克峰、王元、石钟慈等人。数学科学中心常务副主任、今年“晨兴奖金奖”得主刘克峰教授告诉记者,在他参加的多个国际学术会议上,许多大师级的数学物理学家们会谈到陈省身,谈到丘成桐,谈到他们的陈-西蒙斯理论和卡拉比-丘理论。看着他们肃然起敬的神色,刘克峰增强了自己终生研究数学的信念。“有陈、丘两代人的努力,才有华裔数学家今天这么高的国际地位。”把陈省身、丘成桐视为追求目标的刘克峰对数学近乎痴迷,“如果有来生,我还做数学家”,刘克峰的这句名言如今已经传遍数学界。 至于丘先生创办的香港中文大学数学所,记者这次采访第三届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时已经充分领略他们的才华。此届大会汇集了全球700多位华人数学大师,会议期间,颁发了由国际著名数学家评定的晨兴数学奖,并有20位大陆、港、台、海外杰出华人数学家作大会演讲、邀请演讲与简短报告等。会议被公认为具有国际高水平的数学大会。该所主任辛周平教授与刘克峰一起摘取了仅有的两枚“晨兴数学金奖”。 在丘成桐教授指导的近50名博士生中,绝大部分是中国人,其中许多人已经成为国际上知名的学者,成为我国科研院校的教学和研究骨干。为了为祖国培育数学人才,丘成桐担任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大学的名誉教授。他还倡议与主持了一系列高水平的国际数学会议,为争取2002年在北京成功召开“第24届国际数学家大会”、“国际弦理论会议”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并通过自己的影响邀请著名物理学家霍金、威腾及“菲尔兹”奖得主等国际知名科学家前来参加。 醉心于美丽科学 有些人以为数学每一步都可推理,不宜强记,这是极为可笑的说法,我还没有亲眼看过一个伟大的数学家有这种能力。即使在做研究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记忆前人或近人的工作,使我们能够向前作新的研究。 往往记熟某一门技巧后,我们会突然融会贯通,所以多做习题是很紧要的事,假如能够让学生在课堂上有所表现,不单老师对他们了解,他们也了解自己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学生既要强记,亦要贯通,两者能混而为一乃是绝妙之处 同一个问题,可能有超过很多个不同的解法,学生能用不同的方法解题,值得鼓励。譬如,毕氏定理是数学中最基本的定理,古往今来有无数的不同证明,能够举出一些不同的证明,会让学生了解不同的看法可以达到同一的目标。近代数学的大发展,往往起源于用不同的手法解决同一的问题,所以不可小看这些不同的证明。 数学既可以实用,亦独立为一至为美丽的学科,习题可以重视实用,但绝对要讨论看来无用但美丽的工作,重要的是数学的发展可以从实用而形成,也可以追求纯美而成功,要注意的是:所有重要的实用数学都建基于纯美的数学上 数学家和数学是分不开的,能够多谈数学历史和数学家的经历,会对培养学生的兴趣有极大的帮助。 一本数学教科书能够引导学生的兴趣是一本最成功的教科书,可以讲故事(数学家的故事、创造这些命题的过程、中国数学、希腊数学、巴比伦的数学、阿拉伯的数学,都是有意思而影响着近代数学家思维的常识),可以跟其它学科如物理、工程、经济、音乐等等沟通的数学都值得讨论。能使学生以学数学为乐乃是成功的教科书。 虽然只读了三年大学,已经完成了大学的课程。在沙拉夫教授的帮助下,我进入了柏克莱的研究院。柏克莱的数学系当时在世界数一数二。我八月入校,便认识了陈省身教授。他后来成为我的论文导师。 在香港时我醉心于极度抽象的数学(当然我的分析功夫也很扎实),觉得数学愈广泛愈好 我打算念泛函分析,已经学了不少这方面的东西,包括丹福——史华滋有关的巨册,还有不少有关算子代数的书。到柏克莱后,认识不少卓越的学者,我的看法改变了。 我如饥似渴地从他们那里学习不同的科目。从早上八时到下午五时我都在上课(有时在班上吃午饭)。这些学科包括拓朴、几何、微分方程、李群、数论、组合学、概率及动力系统。我并非科科都精通,但对某几门学问格外留神。学拓朴时,发现跟以前学的完全不同。班上五十人,每个人看来都醒目在行,比我好多了。他们表现出色,说话条理分明。 于是我埋首做好功课,不久之后,我发现自己毕竟也不赖。关键是做好所有棘手的题目,并把这些题目想通想透。我读了约翰米拿(John Milnor)的一本书,对里面讲到的曲率的概念深深着迷。米拿是位卓越的拓朴学者。 我开始思考与这书有关的问题,并大部分时间呆在图书馆。当时研究生并没有办公室。柏克莱名牌教授不少,然而不久之后,我对他们竟有英雄见惯的感觉。在图书馆里我读了不少书籍和期刊。 在柏克莱的第二个学期,我渐渐能证出一些不简单的定理。这些定理与群论有关。在崇基时,我跟老师聊天时曾谈及有关的内容,我现在把它用到几何上去。教授都为我的进展而惊讶不已。其中一位教授开始与我合作,写了两篇论文。陈省身教授其时正在放年假。当他回来时,对我的表现甚为嘉许。 纵然如此,对这些工作我倒不觉得怎样。摩里教授(Charles B.Morrey)有关非线性偏微分方程的课,令人难忘。他教授的非线性技巧,当时并不流行。他的书也诘屈聱牙。但我隐隐感觉到他发展的技巧十分深奥,对未来几何学的发展举足轻重。我用心地学习这些技巧。虽在盛名之下,但听他课的学生并不多。到学期终结时,我竟成为他班上惟一的学生。他索性就在办公室里授课了。这科目后来成为我数学生涯的基石。 这年夏天,我请求陈教授当我的论文导师,他答应了。约一个月后,他告诉我,我在一年级时的文章,已够格作为毕业论文。我有点纳闷,心想这些工作还不够好,而且我还希望多学点东西。就这样,在第二个学年中我学了不少复几何及拓朴。陈师对我期望甚殷,他提议考虑黎曼猜想。十分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想过它。 代而之者,我尝试去了解空间的曲率。我确认卡拉比(E.Calabi)在上世纪50年代作出的某建议,会是理解这概念的关键。当时我不认为卡拉比是对的。我开始对此深思苦想。这并不是个当代几何学者研究的标准课题,明显地,这是分析学上的一道难题,没有人愿意跟它沾上边。 解决数学问题不同于下象棋比赛,下象棋走错一步可能满盘皆输,做数学题却是可以不断地犯错误,关键是要不断地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不断地改正错误,才能不断地接近正确 毕业时我得到几份聘书。陈师提议我到高等研究所,那儿的薪水不及哈佛提供的一半。但我还是到那儿去了。在高等研究所我认识了其它科目出色的数学家。同时提升了对拓朴,尤其是空间对称理论的鉴赏力。事实上,利用分析的想法(在流形上的群作用),我解决了这科目的一些重要课题。 由于签证的问题,我到了纽约石溪分校。当时石溪是尺度几何的重镇,事实上那儿真的不错,聚集了一批朝气勃勃的几何学家。我学习他们的技巧,但并不认为那是几何的正确方向。 一年后我到了斯坦福,当时那里并没有几何学者。斯坦福环境安宁,非线性偏微分方程很出色。在那里我碰见好友李安西门及共同的弟子孙理察。我们一起拓展了在几何上的非线性分析。 完成卡拉比猜想的证明后,我看出自己建立了融合两门重要科目──非线性偏微分方程和几何──的架构。 1979年我们在高等研究所举办微分几何年。差不多所有几何学家都来了。我们为几何学厘定了发展的方向。我提出一百条在几何里的有趣问题。到目前为止,有的已经解掉了,但有的还是屹立不动。 丘成桐简介 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华裔数学家、美国哈佛大学讲座教授,1982年,35岁的他获得了素有“数学诺贝尔奖”之称的菲尔兹奖。他成功地把微分几何与偏微分方程的技巧与理论结合在一起,解决了许多著名的猜想,在偏微分方程、微分几何、复几何、代数几何以及广义相对论等方面,都有诸多贡献。丘成桐是至今惟一一位荣获“菲尔兹奖”的华人数学家。 陪同霍金中国之行。 给浙大学生作讲座。 参加“与数学大师有个约会”活动,微笑回答学生的提问。 与路甬祥交谈。 给数学爱好者签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