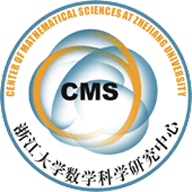| 2004-3-26
编者按昨晚,著名数学家丘成桐在浙大紫金港校区为浙大学子作了“一个数学家的心路历程”的讲演,而前天下午,他在人民大会堂作了“数学与科技”的演讲。本版选登他的部分演讲内容,以飨读者。
丘成桐名片1983年,国际数学会议决定将1982年数学界的诺贝尔奖———菲尔兹奖颁发给一位年仅34岁的华人数学家,这位才能非凡的年轻人就是丘成桐。丘成桐的第一项重要研究成果是解决了微分几何的著名难题———卡拉比猜想,从此名声鹊起。目前,他还是美国哈佛大学讲座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外籍院士、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中国召开的倡议者,浙江大学数学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最近,他荣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数学与科技
知识也是一种美德
我国自从孔子开始,便建立了完整的教育体系,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从此教育不再是贵族的专利,这可是件石破天惊的大事。重要的是,孔子以为知识是一种美德: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虽然如此,孔子也传授实际的学问。他的门人当中,有的当上外交官,有的做生意,有的做了将军。希腊哲人苏格拉底也以知识为善。追求真善美乃是希腊教育的宗旨。在新时代里,知识乃是人类通往幸福的钥匙。任何国家都必须长期投资于教育,不这样做,社会的进步只能是空谈。我们必须牢牢记住,汲取知识和应用知识,才是现代化的真正动力。
基础科学才是现代科技之母
知识必须建基于道德伦理、人文知识、基础科学、应用科学。然而,发展中国家往往以为知识只指应用科学而言。人们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忽视长期的利益。我们必须认识到,只有基础科学才是现代科技之母。中国的现代化,必须要意识到基础科学的重要性。在这个世纪,有几门科技会发挥根本的作用,它们包括:信息技术、生命科学、能源科学、材料科学、环境科学、经济与金融、社会科学。这几门学科互相渗透,它们同样依赖于基础科学的发展,因为后者指出了事物的根本原理。学科之间的融合,始于其基础部分。当融合完成之时,往往导致技术上的突破。对于带动或支持这些发展的国家,其在经济上的利益是不可低估的。
数学是基本语言
时空的语言是几何,天文学的语言是微积分,波动理论则靠傅立叶分析来说明。数学家研究这些科目,最先都由于其本身之美所感召,但最后却发现这些科目背后,竟有些共通的特性。这个事实说明了看起来并不相关的科目,它们之间有甚多交缠互倚的地方。我们先看看通用的语言。语言是一种符号,用以传情达意。中国诗与西洋诗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着重每个单字的用法,因为每个单字都具有不同的意义。然而,就算在中国诗内,字体的多寡也左右了要表达的感情。古诗较随意,汉诗以五言为主,唐代则重七言,到了宋代,流行的便是长短句———词了。不同的体裁,微妙地反映了不同朝代文人的感受。因此,数学的研究改变了科学发展的航道。举例而言,对付立叶分析的理解越深入,我们就更能理解波的运动及图像的技巧。反之,现实世界也左右了数学的发展。波运动及其谱所显示的美,乃是这些科目发展的原动力。这些学科对现代技术及理论科学的影响极其深远。
数学是秩序的科学
除了作为一种语言,以及一门纯美的学科外,数学还是秩序的科学(ascienceoforder)。在21世纪,数学会成为最基本的学科。数学会成为所有科学的框架,它不但是科学的语言,还有其本身的价值。数学乃是秩序的科学,它的目的是发现、刻画、了解外观复杂情况的秩序。数学中的概念,恰好能够描述这些秩序。数学家花了几百年来寻找最有效地描述这些秩序的精微曲折处。这种工具可用于外在世界,毕竟现实世界是种种复杂情况的缩影,其中包含大量的秩序。由是观之,数学能大用于经济学,是毫不奇怪的。好几个诺贝尔经济学得奖者,其工作皆与数学有关。
工具的数学与纯美的数学
大量重要的数学,原意是为解决工程上的问题。比如,维纳(N.Wiener)及其弟子,是信息科学的先驱。他们发展出来的如随机微分方程、维纳测度论、熵论等,最终都远远超出它们原来的动机。Bucy-Kalman滤子理论在现在控制论中举足轻重,而冲击波则在飞机设计中起着关键的作用。最纯粹的数学,要算是数论了。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古代巴比伦、希腊及其他国度。它精美绝伦,没有大数学家不曾为其倾倒。在过去20年间,我们看到了数论在保安问题上的重要应用。解码学依赖于大量与因子分解为质数的问题。自我修正数码也依赖于代数几何学。几何来源自土地测量及航海。虽然它确实解决了有关的问题,但它的功能远远超出了两者,它演变成为时空物理的基石。差不多所有原先为追求纯美而发展的数学分枝,都在现实世界中找到重要的应用。
中国数学的方向
中国认识到现代科技的重要,这点是不容置疑的。过去十年间我国科技的惊人发展,就论文的数量而言,十分可观。单就数学一项,中国人发表文章的百分率,就从6%上升到10%﹙必须指出,所谓中国人包括居于世界各地的中国数学家,在美国侨居者不少﹚。诚然,论文的多寡,可以视为研究频繁疏落的指标。然而细心审视下,可以看到发表于一流期刋的文章,毕竟只属少数。故此当务之急是提升论文的水平。过分重视文章的数量,对研究有负面的效果。我国数学家才调纵横,兼擅独造。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华罗庚教授及冯康教授已开拓了某些领域,走在世界的前沿。当时比较封闭的环境,不但没有妨碍其工作,还使他们走出自己的道路。彭加箂说过,科学是堆砖头,数学家将之变成华厦。诚然,没有砖头或有关砖头的知识,便不可能有成功的设计。惟有数学家与其他科学家的紧密合作,才能为科学打下基础。我们应该鼓励数学家与其他科学家合作。数学的本性决定了,它会随着科学研究的需求而拓宽自身的领域,并会随着综合分析而更为深入。因此,在这个新世纪,数学将成为所有科学的中心。本文编译杨静黄勋
不是循规蹈矩的学生
我在香港的郊区──元朗和沙田──长大。那里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小时候就在河中洗澡。家中有八兄弟姐妹,食物少得可怜。五岁时参加某著名小学的入学考试,结果没考上。原因是用了错误的记号,如把57反写成75,69反写成96等。我只能上一所小小的乡村学校。那里有很多来自农村的粗野小孩。受到这些小孩的威吓,加上老师处理不善,不到一年,我便身患重病。在家中养病的半年,我思索如何跟同学老师相处。升上小六时,我已经是一群小孩的首领,带着他们在街头乱闯。家父是位教授。他教了我不少中国文学。可是,他并不知道我曾旷课好一段日子(或者这是因为我在家中循规蹈矩,他教授的诗词我也能背诵如流)。逃学的原因是老师不怎样教学,在学校闷得发慌,不久连上街也觉得无聊了。当时香港有统一的升中学考试。我考得并不好,但幸好分数落在分界线上。政府允许这些落在分界线上的学生申请私立中学,并提供学费。我进入了培正中学。培正是一所很好的中学。中学生涯的第一年乏善可陈。我的成绩不大好,老师常常对我很生气。大概刚从乡村出来,“野性”未改吧。我热衷于养蚕、养小鱼,到山上去捉各种小动物。沙田的风景美丽清新,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倒是自得其趣,到如今还不能忘怀。当时武侠小说盛行,我很喜欢读这些小说,没有钱去买,就向邻居借。父亲不赞成我读这些小说,认为肤浅,但我还是偷偷去看,也看了各种不同的章回小说如七侠五义、说岳全传、东周列国志等杂书。
古典文学深深影响了我
父亲从我小学五年级教我诗词、古文和古典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厢记等。父亲坚持我在看这些小说时,要背诵其中的诗词。当时虽以为苦,但顺口吟诵,也慢慢习惯。总觉得没有看武侠小说来得刺激。但是真正对我有影响的却不是武侠小说。中国古典文学深深影响了我做学问的气质和修养。近代的作品,如鲁迅的也有阅读。我研读过史学名著史记和左传。对史记尤其着迷。这不仅是由于其文字优美、音调铿锵,还因为它叙事求真,史观独特。直到现在,我还不时披阅这书。晋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其实在做科学时,也往往有同样的经验,读书只要有兴趣,不一定要全懂,慢慢自然领会其中心思想,同时一定要做到: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这是古人的经验,陶渊明的古文和诗有他的独特气质,深得自然之趣,我们做科学的学者也需要得到自然界的气息,需要同样的精神。在以后的日子里,我都以此作为原则,以研读学问为乐事,不以为苦。在父亲的循循善导下,我开始建立我对人生的看法。到如今,我读《史记》至以下一段时,仍然使我心志清新:司马迁“孔子世家”赞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
数学兴趣的产生
在培正的第二年,我们开始学习平面几何。同学对抽象思维都不习惯。由于在家中时常听父亲谈论哲学,对利用公理进行推导的做法,我一点也不觉得见外。学习几何后,我对父亲的讲话,又多明白了几分。利用简单的公理,却能推出美妙的定理,实在令人神往。对几何的狂热,提高了对数学──包括代数──的鉴赏能力。当你喜欢某科目时,所有有关的东西都变得浅易。14岁时,父亲便去世了。这或许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打击。在一段颇长的日子里,对父亲离开了我和家人的事实,我都不能置信。家中经济,顿入困境,我们面临辍学。幸得母亲苦心操持,先父旧交弟子的援手,我们才幸免如此。家中遽变,令我更成熟坚强。困境中人情冷暖,父亲生前的教导,竟变得真实起来。以前诵读的诗词古文,有了进一步的体会。我花了整整半年,研习古典文学和中国历史,藉此抚平绷紧的心弦。典丽的诗词教人欣赏自然之美。我阅读了大量数学书籍,并考虑书中的难题。当这些难题都解决掉后,我开始创造自己认为有挑战性的题目。由个人去创造问题此后变成我研究事业中最关键的环节。
选择数学作为我的事业
1966年我进了香港中文大学。虽然对历史抱着浓厚的兴趣,我还是选择了数学作为我的事业。就在这时,中学时念的高等数学渐渐消化,开始时还不大懂,但一下子全都懂了。大学的数学使我大开眼界。连最基本的实数系统都可以严格建立起来,着实令人兴奋。当我了解数学是如此建构后,我写信给教授,表达我的喜悦。这是本人赏析数学之始。虽然只读了三年大学,已经完成了大学的课程。在色拉夫教授的帮助下,我进入了柏克莱的研究院。柏克莱的数学系当时在世界数一数二。我八月入校,便认识了陈省身教授。他后来成为我的论文导师。毕业时我得到几份聘书。陈师提议我到高等研究所,那儿的薪水不及哈佛提供的一半。但我还是到那儿去了。在高等研究所我认识了其他科目出色的数学家。同时提升了对拓朴,尤其是空间对称理论的鉴赏力。事实上,利用分析的想法﹙在流形上的群作用﹚,我解决了这科目的一些重要课题。新婚伊始,我找到完成卡拉比猜想的正确想法。我终于掌握了凯勒﹙Kahler﹚几何中的曲率了。一些老大难的代数几何问题,都因卡拉比猜想的证明而解决掉。当时我认为我首先了解到Kahler几何的曲率结构后,有物我相融的感觉: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在数学界可说是略有名望。对于我解决的难题,媒体也有广泛报道。然而,认为我的奋斗目标是奖项,是成名成家,那就不对了。这些都不是本人研究的首要目标。我对数学的兴趣,源于人类智能足以参悟自然的欣喜。从几何上看,大自然的美是永恒不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