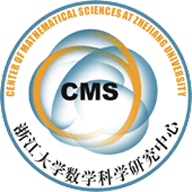■刘克峰
几周前在洛杉矶家中接待了北大乒乓球队,这些来自母校的乒乓天使们与白色的乒乓球,把逐年遥远的北大陡然拉近。我好像又看到了二十五年前生活在北大的我,深冬的未名湖畔,那个为了到“一体”看校队比赛逃课的我。十六岁到二十岁,从少年到青年,乒乓球似乎记录着我在北大四年里最难忘的时光。
小的时候哥哥们打乒乓,我偷偷拾起了他们的旧球拍,没想到这成全了我一生的爱好。我很笨,几乎每一种体育运动对我都是折磨,惟独对乒乓情有独钟。无论何时打起乒乓来,总是越打越精神,那种感觉只有一个字:“爽”。身不由己地成了数学家,总遗憾不能像专业球手一样每天打球。而这单纯的痴迷让我不会放弃任何一个打球看球的机会。
一九八一年刚进北大,那时没有DVD,我把北大图书馆里所有关于乒乓球的书借读了几遍,比比划划学会了还算标准的动作。头一年在燕南园里看到有个石头球台,同寝室的几个同学几乎每天跑去打球,打到月亮升起,再借着月光打,一直打到看不清球为止。每到周四就跑到“一体”抢占球台,“一体”地下室的门锁不知被拥挤的学生们撞坏了多少次。大三时,有了乒乓球课,这每星期一次的课成了我的期待。到了大四,每周六都会借自行车去清华,在一个破旧的大饭厅里没有油漆的球台上打一个下午。未名湖和博雅塔会记得那个十六七岁的少年,寒冷的冬天到“一体”去看校队的乒乓球赛,看得如痴如醉,感觉远比数学课来得享受。许多年来,虽然打球的时间不多,悟性却还不错,在哈佛,在UCLA,我都拿过不少次的全校冠军。来杭州后,也在浙大和浙江省的业余乒乓比赛中拿过名次,当然比在美国难得多,因为国内无处不是高手如云。
不知不觉,白色的乒乓球开始寄托了我太多的快乐和期望。心情郁闷的时候,找球友大战一场。一身大汗之后,烦恼全随着那白色的小球飘到空气里去了。疲倦的时候,一阵乒乒乓乓,神清气爽,读书研究的效率陡长。多年养成了习惯,几天不打球就浑身的不自在。三年前,丘成桐先生用一个乒乓球台把我诱到了杭州。只身在杭州三年多,把一幢空荡荡的大楼建成了近百人的数学中心,也交了不少球友。只要有空总会呼朋唤友来打球。杭州的炎夏,稍一动就会大汗淋漓,打过乒乓,球衣可以拧出水来,好像是蒸过桑拿。打完球再与朋友到附近的小餐馆坐下,几盘凉菜上桌,几瓶冰镇啤酒下肚,怎一个爽字了得!朋友笑我乐不思蜀。我有时也搞不清,到底是为数学,为乒乓,还是为了那美得梦一样的西湖才长住杭州。
十几年前来到美国,哈佛数学系四楼的公共客厅里居然有张不错的乒乓球台,我一下子觉得到了天堂。学数学,打乒乓,夫复何求!在那里看到了天才的数学家塞尔,他也像许多业余球迷一样,很得意自己的乒乓水平。好几位爱打乒乓的哈佛数学系教授就因为输给了塞尔,就不再打球,至少在系里不打了。塞尔每天好像除了打球就是看报,似乎很不用功,可漂亮的数学结果却是一个接一个。另一位哈佛教授鲍特甚至抱怨上帝不公平,觉得他太宠爱塞尔了。我曾经问塞尔,乒乓球是否带给他数学上的灵感,他却不无得意地给我解释乒乓球优美的线路与模曲线的联系。差不多每天下午五点左右,一群同学和塞尔便切磋起来,打打球,谈谈数学,数学与乒乓交织在一起,枯燥的数学也显得快乐了。同学们给系里的每位球手排名,我是第一,塞尔第二。我不过瘾,又用左手开打,曾一度右手第一,左手第二。塞尔为此好一段儿不打球,直到我停止用左手打球为止。后来不知哪位同学在排名表的旁边贴了一个有趣的故事,说当年的大物理学家海森堡酷爱打球,也很为乒乓自负,直到有一天来了一位年轻的学生打败了他,从那以后他再不打球了。这位来自中国的年轻人叫周培源。几年后系里买了个新球台,大家特制了一个铜牌钉在球桌上,牌子上雕刻着一行字:“献给塞尔”,为他对哈佛数学与乒乓球的贡献。
有一年我与哈佛校队,从波士顿开车七八个小时去普林斯顿参加全美大学乒乓球赛。在比赛时看到一个大胖子球手,与当时一位全美排名第十的选手决赛。那场比赛我至今记忆犹新。对方左右跳跃,拉出的弧圈球异常迅猛。只见胖子站在那里,双脚基本不动,只是左右防守,却丝毫不落下风。几板防守后,他会冷不丁飞起一板,力量极大,球像是砸碎到对方球台上。那场球打得颇有些惊心动魄,胖子最后由于急躁,小比分输掉了比赛。输球后胖子那紧锁的眉头和痛苦的表情至今历历在目。那一次我们的成绩不错,B组第一,C组第二。回来的路上我也理清了我博士论文的思路,可谓一举两得。
几年前开始在洛杉矶一家乒乓俱乐部里打球,我看到一位年过九十的美国老人每周两次开着卡车来打乒乓,风雨无阻。老人腿脚不便,只是站在那里左推右挡,脸上洋溢着天真的笑。谁知刚过了93岁生日,老人在打球的时候不慎滑到,摔伤了腿,从俱乐部消失了好一阵子。一天,他被孙子搀扶着又来到俱乐部,可他不能再打球了。老人坐在凳子上看别人打球,脸上挂着无奈的微笑,眼光随着乒乓球飘动,眼里的那份忧郁和失落让整个俱乐部都罩在淡淡的惆怅里。那天以后,老人再没来过。几年间,我们打过几次球,却没有讲过几句话。我们相差五十多岁,来自完全不同的文化,但我们却有着共同的爱好。老人今年该95岁了。
我的脑子里每天除了数学,似乎只有乒乓。不论打开电视还是上网,第一件事就是寻找有关乒乓球的消息。每每提到或看到乒乓,我全身的神经都会兴奋起来,话会特别多,眼睛都会发亮。电视里只要有乒乓球赛,我总会推掉一切,贪婪地盯着屏幕。熟悉的朋友邀请我访问,都会想法为我找几个乒乓高手过招,我的朋友们抓住我爱球如命的软肋。我每到一处工作,也都会努力买张乒乓球台,既活跃气氛,调节情绪,又联络感情,增进友谊。
欣赏一场激烈的乒乓球赛,对我而言不亚于享受一场盛宴。小小银球击打球台与球拍那清脆的声音,就是一首动听的乐曲。乒乓球运动是力与巧的完美结合。对于真正的高手,那球拍像是魔棒,飘忽不定的乒乓球就是被驯服的精灵,在随着音乐舞蹈,时而轻飘,时而迅急。观赏一场高手的较量,就是在欣赏一首拨动心弦的琵琶曲,我神交到了当年的江州司马白居易,意会到了他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感慨。
数学是人类与上帝的智力角逐,乒乓球则是上帝赐予人类最精彩的运动,是力与美的结晶。数学讲究巧与妙,乒乓也是,攻防得当,有张有弛,才是高手的境界。打乒乓球看似简单,无非搓、拉、滑、拧、吊、打、切等几个动作,但使出全身的力气也未必能打到点子上。乒乓球飞快的旋转和速度,需要球手在瞬间做出准确的判断,能够手随心到,在最佳的击球点把球击打回对手的球台上。千万次的机械训练只能练出下意识的反应,练就不出天才的灵气。没有一项运动像乒乓一样敏感和微妙,球手稍稍的心理波动都会反映在球上。天才的球手,他打出的球会带着他的灵性,他的每一场比赛都是与自身性格与心理弱点的搏斗,真正的球如其人。曾经的“千年老二”王励勤和王皓,几番沉浮终于登顶世界第一,那痛苦的历程,就像是蝴蝶的破茧而出,凤凰的浴火重生。做数学,做数学家又何尝不是如此!
尽管乒乓球是英国人发明的,却是中国的国球。乒乓球的美妙、轻灵和飘逸,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真正的高手刚柔兼济,举轻若重,能以柔克刚,能以刚克柔,如入化境,这也恰是中华文化的精髓。
我爱乒乓,正如我爱数学,魂牵梦绕。我有个梦想,即有朝一日,中国的数学能够像中国乒乓一样,带给中国数学家和全体中国人无尽的辉煌和自豪。这梦想从北大起飞,跟随我辗转二十几载,飞翔数十万里,历尽坎坷与沧桑。如今四十岁的我,一如十六岁时,痴情不改,美梦依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