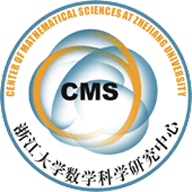
再回首---献给研究生院的朋友们
时间: 2006-02-20 来源:数学科学研究中心二十年过去了,好像是坐着火车驶过来的,路上见到的和发生的许多都在慢慢地从记忆中淡去,却总有几道亮丽的景色在心里挥之不去。这么多年的一切快像小河里的水一样流过去了,可二十年前科大研究生院里那些愉快的记忆却像河里的鱼儿一样时常跃出水面。每每想起来,总会忍俊不住,与朋友把酒言欢也总免不了畅谈那段有些荒唐的快乐时光,彼此开怀大笑,像回到了从前,酒也会多饮几杯。那是我人生的中转站,那时我们一无所有,只有可以恣意挥洒的青春为伴,二十年后我们有了那时梦寐以求的一切,可我们却没有了二十岁的青春。小的时候总盼望着快快长大,可现在只希望时光慢慢地流,尽管很不情愿,却还是被年轮硬拖进了四十岁的门槛。有人曾开玩笑问我,如果上帝让你用现在的一切换回二十年的时光,你会换吗?我没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实在算不清这其中的得与失,只能说人生的一切都是无可奈何的命中注定。当然这也是个不需回答的问题,人生本就是单向的旅程,过去的再美好也是过去了,什么都换不回来。我随意写下这篇文字只是想把二十年前的一些人和事简单地记录下来,自己看着不会忘记,让故事里的朋友们也能回味一下那时的快乐和充满了酸甜苦辣的荒唐。还希望我的学生们能有所借鉴,他们二十岁的人生应该比我们的更精彩,更快乐,更少些荒唐和遗憾。
八五年到八九年是中国数学的天灾之年,八五年六月华罗庚先生去世,此后,张广厚,钟家庆,洪崇威,王启明相继故去,中国的数学一下子倒退了十年。八五年也可以说是中国数学幸运的一年,这一年夏天,陈省身先生开张了他的南开数学所,开始了他在中国二十年的数学事业。同年秋天,我们几个朋友来到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真正开始了我们的数学生涯。
我们第一年生活在北京玉泉路简陋的研究生院。大家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由陌生开始渐渐地都成了朋友。我们住在宿舍与教室连在一起的一个大楼里,两间大房装进了我们8501班的十几个同学。张伟平,周向宇,周建平,杨汉民,江心辉,许秋平住一间;王友德,郜云,叶远刚,孔琢,我还有徐建礼住在另一间。可以说大学毕业选择来到科学院读研究生是我人生第一个也是最正确的选择,因为在这里,懒散了四年的我看到了这些新同学们是如何地刻苦,他们在学业上是如何远远地走在前面,感到不用功真是惭愧。来自复旦的张伟平和叶远刚早就熟悉了研究生阶段的许多知识,而我,尽管刚参加过陈先生的南开暑期班,却还对基本的拓扑几何知识懵懵懂懂。叶远刚提议搞一个讨论班,大家报告学过的知识,读过的论文,这是他们复旦的传统。我记不得我是否报告过,或者报告过什么,但却清楚记得叶远刚报告的莫代尔猜想,张伟平报告的示性类,他们的报告让我开了眼界,刚知道除了大学数学之外有这么多令人兴奋的数学知识在前面。现在我要求我的学生们都开这种讨论班,告诉他们这是“开天目“,是学数学的捷径。
第一次学现代微分几何,瞪着眼看着彭家贵教授在黑板上,一个导数接一个导数,颇为得意地把外微分形式演算的出神入化,我在下面似懂非懂。最后开卷考试,班上十几个学生只有我和伟平得了B, 其余的全是A。记得当时我和伟平好生郁闷了一阵,抽着烟坐在宿舍里不停地抱怨彭教授不公。有趣的是到现在却只有我和伟平成了几何学家,想想也许是彭教授慧眼独具的幽默吧。大概是那个B一直在我心里作怪的缘故,后来我常告诉我的研究生们,千万别在乎考试成绩,它和你的未来线性无关。
我们宿舍的几位按年龄大小排了个序,有了徐老大,孔老二,郜老三,叶老四,王老五,刘老六。当然这里孔老二,王老五的名字最有“意义“,所以也用的时间最长。直到现在很多人喊友德是只喊老五,却不一定知道他真的名字是什么了。这几个朋友里,不知孔琢和徐建礼现在哪里。那时家在北京的徐建礼不温不火地谈着恋爱,常常回家,早早地结了婚。孔琢虽是东北汉子,却时常会红着眼睛,显然是哭了,我们都知道那是他外地的女朋友又写信责怪他了。
当时我们宿舍里几乎每一个人都在以不同的形式在谈恋爱,大家各自私下里猛写情书。唯有叶远刚与众不同,他昼伏夜行,每天给女朋友写诗写到半夜,转天就会叼着烟,一脸憔悴却充满感情地给我们读他刚完成的妙句,这一来把满宿舍的诗情都激发出来了,每天夜里睡觉前都会开一场诗歌朗诵会。老叶高中时就爱上班上一位女生,他胆子也大,居然写了封情书递过去。当时正是高考复习的紧张时期,这女生不知所措,就把情书交给了老师。那时老师的思想可不像现在有些清华教授们这么“开放“,就当着全班的面念了情书,还捎带着挖苦了几句:前方冲锋陷阵,后方醉生梦死。这搞得老叶好不灰头土脸,也好,他便心无旁骛,一心苦学,高分进了复旦。可这初恋的不愉快很伤了老叶的心,大学四年他看不上任何女同学,只是一心一意地读书,也难怪他刚进研究生院时的水平如此之高了。
那时老叶除了每天填表联系出国,就是专心写情书,情书居然还是寄给他那位高中时的女同学。来研究生院前的那个夏天,他们在家乡重逢,爱火重燃。老叶那时每天都会激动地吸着烟,高声念着他憋了一夜的诗句,用带湖北口音的普通话感慨着人生的沉浮。记得很清楚老叶不止一次双目放光,用嘶哑的嗓子几乎叫喊着朗诵他最得意的诗句:迎接那来自天堂的皓光。他真觉得自己的女朋友带给他天堂般的感觉了。八六年夏天老叶先出国,一年后回国结婚,他们一起在美国生活了几年。十年前我在斯坦福又见到头发秃了不少的老叶,他精神不错,告诉我他们离婚了。也许是离婚的打击,老叶做数学的劲头一落千丈,放弃教职去了银行,在匹茨堡过着幸福的生活。我想他的前妻如果知道老叶为了给她写诗,憋了多少个不眠之夜,憋掉了多少根头发,她如何影响了老叶的一生,她离婚时也许会多想想吧。
老五现在已经是科学院的教授,杰出青年了。当年每晚睡觉前的赛诗会上,老五都会不甘寂寞地即兴朗诵上几句,其实都是为了开老叶的玩笑。老五被大家封为垃圾派诗人,这是因为他的每一句诗都会或多或少地与垃圾桶或者野兽有关。比如他的名句:我掀开马桶吐一口痰。谁也不能否认这不是诗,尤其是朦胧诗,否则性格倔强的老五会无休止地辩论到你承认为止。老五最棒的是他独创的“拧麻花”舞步,堪称一绝。那时候每个周末我们宿舍的几个人都会张罗舞会,邀请研究生院的女生们来参加。看到舞场里有我们认为过于高傲的女生,都会让老五出马。他也从不辱使命,不懈地请到后,便开始拧麻花。只见他站在那里,两只手架着舞伴不停的转来转去,舞曲一停,这女生便晕头转向地踉跄出舞池,傻笑着坐在那里了。
后来老五在舞场上认识了一个女研究生,有些喜欢,便时常地约她散步,跳舞。开始还算顺利,老五给她起了个暧昧的外号“小白兔”。有一次老五去约小白兔散步回来情绪似乎不大对,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自嘲地告诉大家,自己被野兔子咬了。原来老五去约小白兔散步,可她却扭扭捏捏很不想去,后来勉强去了,走到半路,她突然对老五说:其实我有男朋友。老五当即反击:其实我也有女朋友。不知当时的场面如何,两人的表情又如何,但从此二人再不见面了。这样结束的约会怕也是绝无仅有,不过,倒也足见老五不卑不亢,寸土必争的外交家般的机敏。
老郜应该是最有诗意的一个,而且早早就有诗发表了。那时他诗写的“黄”,大都与青春期有关,人也最玩世不恭。大家都以为他会是最早离开数学的人,可是十几年后再见到时,他已经在加拿大成了数学教授,而且除了数学,他好像无心谈任何事情,诗也早不写了,数学论文却越写越长。还记得一次我的女朋友来北京玩儿,老郜掌勺,在宿舍里的一个小电炉上,用一个下午烧出了一桌好菜,想想真不容易。尽管现在时常山珍海味,那顿饭却记忆尤深。几年前去多伦多老郜家里做客,他贤惠的太太告诉我,老郜已经好久不下厨房了,让我好生感慨了人生的变化无常,心中也遗憾,怕是再难吃道老郜做的饭了。
老郜曾给我们讲过一段他们大学同学写诗的“盛景”。当时他们同班几十号人,只有两个女生,其中一位还难得的漂亮。忽如一夜春风来,全班的男生都开始写诗了,而且大都与嫦娥,月亮什么的有关,可以想象都是献给这位女生的,因为她的名字里有个月字。老郜给我们念过几首,声情并茂,不动情怕写不出的。可这位女生后来回诗一首,给全体男生们当头一盆冷水。诗的大意是:我是一轮高高在上的明月。傲气逼人,显然没把众才子们放在眼里。我们一致认为老郜也给这女生写过情诗,否则他自己的诗不会写得这么好,老郜是坚决否认,号称根本看不上她。我也询问过好几位老郜的同班男生,没有一个承认写过,也许才子们都太好面子了。
伟平进研究生院时就懂的很多了,他那时读的数学书我是一年后才能读懂。伟平除了喜欢读书,就是喜欢逛书店。当了教授以后这爱好又扩展到DVD店和电影院。那时他有空就背着书包去北京城里四处看书买书,回来时书包里除了数学书还有琼瑶小说。我用来讨好我女朋友的那本月朦胧鸟朦胧,就是伟平给买的。据说他收藏并研读过琼瑶全部的小说,并引以为豪。不过后来他却坚决否认他对琼瑶何时何地有过任何的兴趣。现在伟平成了南开陈省身数学所的所长,依然充满小资情调,对电影和气质女明星们有毫不掩饰的喜爱。他周游世界,所到之处对当地最好的电影院和最新上映的电影了如指掌,对书店反倒淡漠了。也许到了四十岁的年纪读得多的是文章,想得多的是数学与人生,书反倒看得少了。
向宇是个不爱说话的人,有了不顺心的事喜欢一个人扛着,唯一的表现就是唱歌。那时没有卡拉OK,他一个人关在宿舍里大声唱,以刘欢的歌唱得最多。每当我们听到向宇的“几度风雨几度春秋“,就会断定他又不开心了,而且歌声越响亮,心情就越不好。不过向宇后来却练成了好嗓子,有了卡拉OK以后立刻大显身手,被伟平封为“赛刘欢”。这又在追他太太的时候派上大用场。先是“爱的代价“,后来“爱如潮水”,一气呵成。再后来是“打靶归来”,结婚生子一举搞定,没点儿气魄怕是不行。现在向宇成了科学院数学所的所长,正是春风得意,踌躇满志,不知道又爱唱哪一首歌了,会不会是“走进新时代“?
汉民大概是我们同学里最灵光的一个了,什么东西一学就会。他从一个很小的学校考到数学所,不为别的,只为他大学的一位女同学。他很喜欢这位女生,算是他的初恋,可同时有一位在校的研究生也在追她,这女生在两者间有些犹豫。年轻气盛的汉民觉得这犹豫是因为自己的地位不够,于是发奋苦读考上了数学所研究生。那时他又开始与她通信,还给我看过她的几封信和照片,那的确是一位很有气质,也颇具文采的女生。这女生在一封信里几乎有些祈求地希望他“再往前跨一步“,可汉民这一步却怎么也不肯跨了,原因是她当年的犹豫很伤了他的自尊。记得我劝过他好几次:你汉民错过了这位初恋,会后悔一辈子。他却潇洒地以天涯何处无芳草来回答我。汉民家里穷,一心想挣钱并早早下了海。后来他在深圳做买卖,却一直没发达起来,谈过一打女朋友后,结婚生子一直生活在深圳。我有时很想问问他是否后悔了自己的书生意气,还有没有了当年的自在潇洒。
八六年我们搬到中关村四十二楼,后来又搬到数学所简陋的小楼里。当时中关村的各个大学里都弥漫着风声雨声麻将声。有一阵向宇,汉民,老郜和我都迷上了麻将,曾经一度搓的昏天黑地。那时没钱,赌注也只是些饭票。有意思的是几个月下来,每天算起来个个都是赢家。尽管没有输家,却常有借饭票的。有位美国留学的朋友回国找女朋友,看到我们玩得太厉害,说我们太浪费时间,我们心中很不以为然,连他找的女朋友也鄙视他假清高,毅然与他断绝了关系,可见那时玩乐之风是如何深入人心了。现在想来,那是大家当时都对前途很迷茫,没有奋斗目标的缘故。我现在当了系主任,有时坐在主席台上给学生们作报告,鼓励大家抓紧时间,刻苦用功,可心里也犯嘀咕:学生们会不会也觉得我假清高呢?这大概是那个时候留下的后遗症了。其实我也真得很懊悔那段荒唐的时光,能用来读几本书该多好。
记得有一次老郜带着大家去承德玩儿,登记住宿时,女服务员问我们是那个单位的,我们说数学所,服务员不耐烦地问我们是哪个”数”,她居然不知道数学所的“数“ 字!真让我们这些“太学生们”没面子。倒是老郜灵机一动,说我们是科学院麻将协会的,服务员于是毫不犹豫地写下了来访者单位:麻协。这样我们几个麻协成员在承德白天游山玩水逛寺院,晚上蒙古包里跳舞,愉快地潇洒了几天。很希望能有机会再约麻协老友们旧地重游一番,可即使去了,怕也只会唏嘘人生如梦,物是人非了。
除了搓麻将,我们几个还常骑着自行车在周围的大学里四处找舞会,我们也办过许多舞会。其实自己并不喜欢跳舞,也许只是消磨时间,不情愿地随波逐流。如果不是八七年十二月一个寒冷的早晨,王启明先生来敲我们宿舍的门,把打了一夜麻将的我从梦里敲醒,我现在不知道会在做什么。那一天启明先生把我推向了另一个人生轨道,他是我生命中的贵人。他八九年四月去世,留给我们的是他对几何的执著与热爱,和对中国数学未来的满怀期望。但愿今天和以后的我不会让他太失望。
人似乎都要经过这么一段荒唐与快乐才会长大。八八年初我结了婚,似乎真的长大了,可心却好像永远停留在二十岁。八八年来美国后,时间过得很快,生活里除了读书似乎没有太多的事情可以让我如此难忘,二十年前的时光好像被拉长了一样常常飘在脑海里。回首这二十年,充满了快乐,满足和遗憾。有人问我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说是要交到好朋友,有了好朋友你就成功了一半。许许多多的朋友给了我许许多多的帮助和激励,像冬天里的阳光一样常给我淡淡的温馨。好多年过去了,很难再碰到二十岁时那样单纯的友谊了,却常会遇到些过分自私或者自负的“朋友“,付出真诚和友谊收获的是失望与背叛。人的成长就是对朋友和生活认识的一个过程,这简单的道理是我不惑之年对人生返璞归真的感悟。
我时常想起二十年前,想起那时的朋友们,感激他们与我一起度过的那段快乐时光。我在心里总会默默地祝福他们,不管他们生活在地球的哪一个角落,正在忙着什么。再回首,云遮断归途,是啊,我永远不可能再回归到二十岁,但无论什么都遮不断我对二十年前的美好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