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想跟各位同学谈谈我三十多年来做学问和培养学生的经验。
我大学毕业以后,到柏克莱跟随当代几何大师陈省身先生,也师从近代徧微分方程的奠基者Morrey教授,体验最深刻的是他们做学问的态度。
以后我任教过的学校有普林斯顿的高等研究所、纽约石溪分校、史丹福大学、加州圣地牙哥分校和哈佛大学,三十多年来踪迹满天下,几乎与数学界所有的大师和理论物理学界一部份大师都有过从。我希望将这些经验供给年青的学者参考。
我教导和已毕业的博士生已经超过五十名,他们很多已成为有成就的学者,最可惜的却是有刚毕业时很用功,以后却因为名利所误,而终究不能成材的学生。
这些经验与我国近十年来浮夸的学风有密切的关系,希望今天的演讲能改正这种看法。
无论是个人、学校或研究所,必需要有一个崇高的心愿。我们固然需要一技之长,既要养活自己和家庭,也需要替社会服务,然而作为一个有智慧的现代人,作为一个有远见的学术领导者,我们不能不考虑整个大环境的基本问题。
在考虑基本问题时,我们或许会寻求大自然的奥秘,或许会寻求工程学的基本原理,或许会寻求社会经济学的共同规律。而数学家和文学家更可以寻求或制造他们心目中的美境。
司马迁说的“究天人之际”正可以来描述一个读书人应有的志向。
一个人的成长就像鱼在水中游泳,鸟在空中飞翔,树在林中长大一样,受到周边环境的影。历史上未曾出现过一个大科学家在没有文化的背景里,能够创造伟大发明的例子。一个成功的学者需要吸收历史上累积下来的成果,并且与当代的学者切磋产生共鸣。
人生苦短,无论一个人多聪明,多有天份,也不可能漠视几千年来伟大学者共同努力得来的成果,这是人类了解大自然,了解人生,了解人际关系累积下来的经验,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够成就的。
这些经验透过不同的途径在当代学者的行为和著作中表现出来,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在接受先人的文化,在接受同侪的交流时会有不同的反应。有深厚的文化背景,有胸襟的学者比较容易汲取多元化的知识,在思想自由的环境里,这种知识很快就会萌芽,成为创新的工具和能力。
古代希腊汲取了埃及、巴比伦的文明,学者又能尽量发展个人的意志思维,因此孕育了影响西方文明二千多年的哲学和科学,他们在一、两百年间集中了一群学者,谈天论地,求真求美,当时积聚的知识有系统的整理出来,他们的精神和他们所用的方法影响到以后文艺复兴的科学发展,直至今日。
在同一个时期,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由于战乱,向西、向南、向东拓地的结果,夏商周三代的文化与各地的地方文化融合,学者受到各种文化的冲击,拓展出中华民族原创作能力的高峰。
近二百年来中华民族受到外国的冲击可说是前古所未有的。而这廿年来国家经济的稳定发展终于使我们民族能够安定下来,我们年青人对祖国开始有信心,也开始想一些重要的民生以外的问题,希望在这个时候,中华民族和西方文化,能够得到自然的融合,而并发出一个求善、求、求美的新文化
司马迁自传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由于时代的发展,能够承先启后、融合东西的事业,恐非一人一时之力所能完成。
然而诸位都知道,在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环境里,事情会来得顺利。回想当年量子力学研究刚开始时,不能不感叹一时多少豪杰。纵观今日科技的发展,只要找到好的方向,
在好的气氛栽培熏陶下,人人都可能成为豪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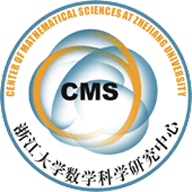




 冰岩作坊
冰岩作坊